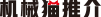今年己八十岁的三叔是个老木匠。这几年因为视力不好,除了偶尔帮人家操办一回丧事就不再做木匠活了。他常常跟我聊起关于木匠的那些事,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谈到的那些事好像从来还没听人说过,而且极有可能今后也不会有人再提了,在这方面他是活档案,那些情景有的正与我们渐行渐远,有的已经被历史尘封了很久。下面我的这篇小文虽然算不上是为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作的努力,但至少可以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到关于木匠的那些事。
一、木匠的分类
三叔告诉我,他做了六十多年的木匠,但只能算是一个荒木匠,我哪里知道还有荒木匠一说,经他一番细说才明白过来。原来虽然做木材加工活儿的匠人都统称木匠,但其中还有较明细的分类,荒木匠只能做一些常见的粗木工活儿,比如大木作、船作、精细家具等大型木作的配套作业,和打造一些粗家具,棚户搭建。这批人是木匠中的主力军,他们既要有技术,更需要力气,他们的技术含量不高,没法去完成各种特殊性质的精细活,或统筹性的建造。过去农村中的一些所谓巧农民,家里也都有几样常用的木工工具,也能懂得一点荒木匠的技巧。
除了人数较多的荒木匠,社会上还好几类专业性质很强的木匠。最常见的有圆木匠、犁木匠、船木匠和细木匠四大类。
先说圆木匠,那是专门制作园形木桶的工匠,就是人们常说的箍桶匠。很早以前,因为金属材料紧缺,塑料制品尚未问世,各式各样的圆木桶是每一个家庭里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那时候,家家都有一副粪桶(两只),女人们都有一只必备的马桶,还有许多大小不一五花八门的小玩意儿也全是由箍桶匠用木板箍起来的,如饭桶、洗面桶,洗脚桶和儿童用的小马子等等等等。更大一些的还有酿酒坊里用的蒸饭桶(大圆桶下面连着大铁锅,又叫大甑子)。在铁制的油桶尚未传入我国之前,国内的油料包装也全是用的圆木桶。因为需求旺盛,那时圆木匠人数众多,遍布城乡。在乡下,大都是挑着一副装满工具的担子,走村串巷。城里也有边制作边销售的圆木铺子。圆木匠的技术含量要比普通木匠高得多。他们先利用圆周率计算出所需木板的周长,木板之间还需用竹钉连接,因为木桶大都是上部直径比下部要大些,甚至还有的是腰鼓形状的(如有一种带拎把的马桶就是腰鼓形),如何将每一块木板制作得一次到位,全靠经验。
再说犁木匠,顾名思义,犁木匠是专门制作和修理耕犁的。过去耕田主要是靠人力和畜力,那种木犁除了犁头和犁耳是铸铁的,其它部位都是用有着一定弯曲度的杂木制作的。木犁的主要构件叫犁辕,它不但要选用材质非常硬铮的杂树(桑、榆、槐等乡土树种),而且树身上还必须有一段自然长成的不规则的S形曲度。因此,犁木匠所用的材料都是些看似毫无用处的歪瓜裂枣。不过,那些材料价钱可不菲,因为硬质的树种生长速度极慢,不容易成材。俗话说:九楝三桑一棵槐,要用柞贞(栎树的俗称)转世来意思是说人的一辈子的时间只能用到三茬桑树或者是一茬槐树,如果是小时候栽下的一棵柞树,那棵树在他的有生之年还成不了材。楝树虽然长得快,但它不是穿犁的料(我们那里习惯将制作耕犁叫穿犁)。一棵碗口粗的桑树大约需要十多年时间长成,如果弯曲的程度适宜就能作一副犁辕的料。犁木匠的技艺大都是祖传,人数不多,只有特别大的庄子上才会有一两家。因为没法在那么粗的树材上用人工去获得恰如其分的弯曲度,在天然长成的弯曲度又不甚理想时,就只能凭借犁木匠们的独特而精湛的技艺,通过合理截段、调整眼位、切削加工等方法来弥补。因此,犁木匠的活儿,荒木匠们是不敢问津的。
还有船木匠,分大船作,小船作,造大船的专业性,和文化知识要求很高,非一般人能胜任,而小船作也是由集体的大船作发展起来的。正是这些当时为集体作的大船匠、犁木匠,还有“异类”圆木匠,延续了明清仅剩的一点点木匠手艺,在后来改革开放中,大显身手,成就了最早的一大批细木匠高手。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战天斗地主,我家地盘我作主,栽树砍树我当家,纯朴的农村人,在自家房前屋后,田埂河边,不管将来有的没的,种上几棵遮阳挡雨的树,不求今生回报木材,至少留得子孙一片余荫。现在,成天斗地主,国家地盘都作主,多种树,少生事,,,,,我艹,砍树你当家!,,,,自史以来,栽树是农民家庭资产唯一的长线投资,木材的收获,同时细木匠们收获了技艺的提高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得不说的题外话,言归正传:
细木匠,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具木匠,所谓细木匠,必须从荒木匠基础开始,扎扎实实的,一步步逐渐升级为,制作传统家具的木作师傅,其作品,从用料选择、尺寸制式等等,都遵循职业规矩,你的特殊要求,不能突破他对职业操守上的底线,更不会主动破坏规矩,这会让他留下笑柄,或成为一辈子的遗恨。所以那时虽然农村人生活质量不算精细,却留下许多做工相当考究,精美的柴木家具,大都具有传世的价值。现在文物市场上出现的那些堪称天价的明清家具,都是那个时代细木匠们的杰作。细木匠们,同时还从事高档古建筑的建造、维修和装潢,大到皇宫府邸,小到随处可见的寺庙道观,其中的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和室内的屏门花窗也全都是细木匠们的心血结晶。由此可见,细木匠们的盛衰是与社会状况相关联的,越是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年代,细木匠们越是受到青睐。反之木匠中最容易失业的就是细木匠。记得在人民公社的那些年,这些人大都不务正业,他们也不得不与荒木匠们同流合污,去帮生产队里修农具,为社员们盖茅草屋。直至改期开放以后,他们才得以星火燎原。
二、拜师学徒
三叔还跟我说了他当年拜师学徒的那些事。木匠的学徒期一般是二到三年,期间,师父管吃管住,学费不多,也无明文规定,主要是师父要无偿占有徒工在学徒期间的劳动。特别在最后即将出师的那一年,徒工已经可以拿到跟父差不多的工资,这些都全归师父。如果这个师父大气,或者与徒工家是亲戚、朋友,师傅就会让他提前出师,人虽然还跟着师傅继续深造,但可以得到他自己的那份工资。
学徒工大都是一些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他们拜过师后就进入了师父的家庭。一开始,他们大都学不了多少木匠的技艺,好像只是师父家的一个小长工,家里的什么活儿都要干,包括洗衣烧饭带孩子,早上还要替师父倒夜壶。如果碰到一个又惰懒又霸道的师娘,整日里会对他呼来唤去,连孩子的尿布都要他洗。曾经有人调侃说:当学徒的,除了不用替师娘洗屁股,其余活儿样样都得干,这是极少数情况,大多的徒工遇到的是一对心地善良的师父师娘,因为作为百家师傅,他们首先自身要具备很高的职业素养,加上,徒工的父母总会有的放矢的,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声名不错的师门,这样,他们在师父家中既能学到立身的技艺,并体验到一些家庭以外的温暖,只有这样环境下的徒工,才会走的更远,多少年过去后,师徒关系仍然会很好,这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还有更圆满的,师父师娘看中了这个徒弟,后来将家中与之年龄相仿的宝贝女儿嫁给他,虽然这种情况不多,但几乎每对都是好姻缘。
开始让徒弟接触木工活儿时,只是让他先当下手,继而再让他学着磨各种刀具,斧刀、伐锯条,拉大锯,从基础上做起。我们这儿,木匠用的斧子叫斧头,斧头的锋利不是最重要的,讲究斧忍口的适用性,古人说:工欲善其行,必先利其器,因此,磨斧是木匠最难的一项基本功,其它刃具相对容易一些,不过要想磨的又快又好用,也不简单,就像过去学剃头先要学会磨剃刀一样。然后,再上手锉锯,伐锯,根据用途不同,木匠都有大、中、小好几把锯子,接下来,刨子,最后的才是凿子最难的,与其说是在磨工具,不如说是在磨徒弟的性子,同时更是让徒弟见识到更多的木头,掌握更多的木性知识,这才是三年学徒生涯中最需要掌握的,最宝贵的知识财富。
比较畅快淋漓的是拉大锯。那时还不曾有锯木机,只能先通过拉大锯将圆木分解成不同厚度的板材。拉大锯是个力气活儿,先将圆木固定在一个专用的架子上,一头像大炮似的斜着向上,通常是师父站在架子上面,徒弟半蹲在下面,两个人此拉彼推使大锯作不停的往复运动。拉时还要注意不让锯缝偏离事先划好的直线。由于锯齿的倾斜角度偏向下方,因此,向下拉时比向上要吃力得多,站在上面的师父虽然不及下面的人费力,但他是掌舵的,是主角,他要保持锯缝不偏不斜。没拉过大锯的人,不多会儿就会腰疼腿酸,不适应,吃不消。学徒的人却没资格抱怨,入了这一行,不适应也得适应,有时一天大锯拉下来,晚上躺在铺上,浑身像散了架似的难受。
木工技术的具体操作主要是锯、斫、刨、凿四个方面,锯就是下料,截段的长度要比成品稍长些,这是木匠们的原则,因为长一点有加工的余地,所谓长木匠,短铁匠是也。斫,就是用怠斧将某一部件尽量切削成接近成品的模样,然后再进行刨光、凿榫眼、做榫头、整体安装。徒弟练手时,师父大都会让他独立制作一张小板凳,这种小凳子在我们这里叫小爬爬,是普通长条凳的微缩版。物件虽小,但要将其制作得像模像样并不容易,起码需要粗通锯、斫、刨、凿四大技巧中的要领。因为小爬爬与小方凳不同,四腿二枨的大小,叉开角度,需要凳面上四个榫眼凿得十分精确,才能保证其对称、匀称、美观,稍有差错就会十分难看。因此,有人常说,做好小爬爬,就能出师了,但,如果作为木匠师傅,必须要做得好一张难度更高的:绳凳,这个凳是相当考验技术的,几乎没几个师傅能做得好,且一般不会轻易偿,这需要对自己技术的绝对自信。
出了师的徒弟会从师父那里得到一把,或几把师傅精心制作的工具,以资鼓励,在以后的江湖闯荡中取得好成绩。
再跑个偏,三年学艺,三月补艺,如时出艺,看你手艺。对于三月补艺之说,,后延三月是师傅教你真正的技术,这可以肯定的说是:江湖有谣言,延长留师时间有,但不是师傅留一手的问题。试想,那时候,师傅的授艺,基本是现场手把手的授教,而接活又不是随心所欲的,谁也不能保证传说中加三个月的活,与授艺配套,所以这个是错误的说法。
所谓的三月补艺,只是说明自己的技艺尚有不足,虽然出师,还需经常到师傅这里来充电补漏,或在别的木匠师傅那里取长补短,以夯实自己的木作基础和见识,然后凭积累的丰富木作经验知识,创造性的解决木作中的实际问题,让自己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木匠师傅。
关于网上流传的老木匠彦言,确实非常精辟,而且实用,虽然老木匠的彦言,我也是从网上第一次看到,但,据木作现象和我切身体会理解,作者的解说,是个非常严重的误导,本来是个很有用的木作经验知识,但却把许多DIY木友引向了错误的道路,我会开贴另说(紫小檀)。
三、木、瓦两作
农村中砌房子主要由木匠和瓦匠来共同完成,木匠负责制作木质的屋架、门窗隔板之类的木工活,瓦匠只负责砌墙、粉刷,当然还要有一些运料打下手的小工。不过,木、瓦工之间的分工并不明细,大部分荒木匠也会做一些如砌墙之类的瓦工活儿。人们就把这种技术全面的多面手称之谓木瓦两作。这种现象在大集体的年代里最为普遍。那时经济困难,盖房子因陋就简,没那么多的木工活儿做,木材是上了计划的,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屋架大都是用杂树棍和毛竹之类的器材瞎对付。木匠们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只能跟瓦匠一起用土墼砌墙用麦草盖屋。最困难的那几年,这些木瓦两作的师傅们每天的工钱只有一元钱。那时,做小工的人是不要工钱的,都是亲戚朋友邻里之间互相帮忙,主人家除了管几顿简单的饭就是多说些感谢的话。
虽然木瓦两作的师傅们在那时收入也不高,但比起普通社员来还是优越得多,他在人家干一天活,人家除管他的饭还要给地一元钱的工钱,那时的一元钱的含金量是远远超过现在的百元大钞的,养一只母鸡,十多天才能攒下七角多钱的一斤鸡蛋。如果师傅再带上一两个徒弟,收入就更可观了。因此,那些年,社员家的儿子到了十六七岁时,都千方百计地想让他去学个木瓦两作,因为大家都认可艺不压身荒年里饿不死手艺人这些个简单的道理。还有,只要小伙子学上了手艺,就不愁找不到媳妇。
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普通社员要想完成这个心愿是十分困难的。主要是因为那时对农村劳动力的控制相当严格,有一段时期,好像除了老老实实地种田,其它的行当都是歪门邪道,都是资本主义尾巴。生产队对以前学成的手艺人实行定额上缴的土政策,每年向队里上缴几十元的公积金才能允许他们在农闲时走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道路。对于想学徒的年轻人则严加控制,未经批准就擅自脱离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有可能会被扣发全家口粮。在这方面,大队里的支书是关键人物,支书点了头,事情就好办,否则的话,找谁也行不通。为了打通关节,有孩子想学徒的人家会千方百计地讨好支书,用各种手段与之笼络感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也有数额不大的权钱交易和纯粹的权色交易。有一户人家,求了支书二年也未曾得到批准,他挺无奈地开玩笑,说: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只要他能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就是让我的婆娘跟他睡一回我也舍得。当然,这是玩笑话,说明当时农民的天职就是种田,弃田从艺的路并不好走。其实,支书也有支书的难,如果来者不拒,年轻人都去学木匠学瓦匠,哪有人种田?那时候农业学大寨全靠的是人海战术。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的住房条件不断地得到改善,建房子、建好房子的人家多了,那些当年一天只拿一元钱工钱的师傅们还因此发了点小财。有些技术比较全面的木瓦两作师傅大都当起了包工头,他们最大的遗憾是不容易收到徒弟,徒弟是不用发工资的员工,多多益善。农村中的年轻人有了更广阔的出路,他们中的皎皎者纷纷通过高考那座独木桥跳
出了农门,也有的人自主创业,弄大船搞运输,自己也当上了小老板。后来,又有不少青年人出门打工进了工厂,那些人回来时个个西装革履,风光无限。他们不再被捆绑在土地上了,他们嫌做木瓦两作吃苦收入少,当年被人羡慕的手艺人,好像已经成了农村中最不体面最没出息的人,夏天,他们在烈日的烘烤下挥汗如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他们玩的是一块块冷砖头。因此,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丢掉了当年费尽心机才学到的手艺,彻底改行,做起了别的营生。此时,包工头们不得不改革收徒弟的规矩,只要有人愿意学,不超过一年就会发给他每天一百大几十元的工资。
四、如今的木匠
时到今日,木匠这个行当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先是木匠中的圆木匠和犁木匠逐步消亡,几近绝迹。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一切都发生在近几十年间,自从石油化工使塑料制品得以问世,市面上很快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塑料容器,随着各种价廉物美的日用塑料盆桶进入了寻常百姓的家庭,延续了上千年之久的木桶木盆就一下子被闲置起来了。那些器具现在大都已经作了柴禾,只有一些年长的农村老太太还妥善保存着当年她们娘家的陪嫁马桶。她们虽然也早就用上了塑料便桶,也明明知道这些古色古香的历史遗物,永远也派不上用场了,但是她们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东西,因为那是子孙桶,不作兴随意毁弃,偶尔被她们的孙辈们看到了,还总要解释一下这种老物件的来龙去脉。最后一代的圆木匠们,现在大都已是风烛残年,或许再过些年,这门老行当就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会再有人提它了。
犁木匠比圆木匠消亡得还要早一些。上世纪七十年代,小型拖拉机逐步取代了耕牛,曾作为上千年农耕社会象征的木犁也随之寿终正寝。代代相传的犁木匠技艺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铁铧犁都是在工厂里生产出来的,社会已经不需要他们的那种专业技术了,社会进步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而且是结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想想还真值得我们这一代人自豪。 农村中的细料匠们,在上世纪末还红火了一阵子。得到了温饱又积累了一定经济实力的农民,开始置办一些相对高档的家具。那几年,市场上的木材供应逐步解禁,几乎家家都想有一张仿古的八仙桌和与之配套的四张秦凳,那种桌子四周有精美的镂空雕刻,有的还要在桌面上嵌一块天然大理石板。那是细料匠的活儿,虽然荒木匠也能做,但无论如何总做不出那种传统的经典式样来。后来,市面上什么样的高档家具都能买得到,很少有人再在家里制作家具了,有的细料匠就被招工进了家具厂。还有的到大城市里去建造、维修古建筑。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当年那么高超的技术水准了,他们干的活儿有些荒木匠也能跟在后面滥竽充数,因为现在设计有电脑,雕刻用机器,也做不出什么传世之作来。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伦教街道羊额工业园永安北路A3号 公司名称:广东顺德铭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欧阳 联系电话:18988505267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家具头条立场。